這些“鍵盤俠”有治了:關于網絡暴力的罪與罰,業內稱有望年內落地_當前熱點
本文來源:時代周報 作者:王晨婷
 【資料圖】
【資料圖】
數次悲劇之后,網絡暴力行為或將迎來嚴格懲治。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發布《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為《征求意見稿》)提出依法嚴懲網絡暴力違法犯罪。實施針對未成年人、殘疾人的,組織“水軍”“打手”的,編造“涉性”話題侵害他人人格尊嚴的,利用“深度合成”技術發布違法或者不良信息,違背公序良俗、倫理道德的,網絡服務提供者發起、組織的網絡暴力違法犯罪,應當從重處罰。
《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意見反饋截止日期為2023年6月25日。
與傳統違法犯罪不同,網絡暴力往往針對素不相識的陌生人實施,被害人在確認侵害人、收集證據等方面存在現實困難,維權成本極高。
《征求意見稿》指出,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要充分認識網絡暴力的社會危害,為“網暴”受害人提供充分法律救濟,維護公民合法權益,維護社會公眾安全感,維護正常網絡秩序。
那么,網絡暴力如何認定?會面臨怎樣的懲罰?又會否出現“法不責眾”的行為?帶著這些問題,時代周報記者采訪了數位法律方面的專家。
1、如何看待《征求意見稿》,對于減少網暴會有怎么樣的影響?
北京卓緯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孫志峰:
網絡暴力備受社會高度關注。該意見不僅有助于縷清網絡環境下各種犯罪形態的邊界,進一步明晰各種犯罪在網絡環境下的構成要件,有助于執法、偵查、司法機關準確把握。
此外,該意見以兩高一部聯合發文的方式特別明確或進一步明確了公安機關不予立案的救濟渠道,自訴案件公安機關協助取證,以及侵害人格權禁令、公益訴訟制度引入等,直擊網絡施暴無法獲得救濟、無法準確取證、公權力機關不愿參與、不想參與的痛點,我認為這是意見中最大的亮點。
如果依法落實到位,無疑將給網絡施暴者一個重大震懾,對修復網絡健康秩序有非常積極的影響。
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孟博:
基于網絡的匿名性、虛擬性,部分網絡用戶對于自己在網上的言行抱有僥幸。一些網絡用戶所編造的信息,經過網絡傳播、發酵,不僅對被害人造成極大傷害,而且會嚴重擾亂網絡社會公共秩序。
加大對網絡暴力行為的打擊力度,是治理網絡暴力亂象,營造風清氣正網絡環境的關鍵。
一方面可通過多種途徑加強普法宣傳教育,提高網絡用戶的法律意識,使其知曉“網絡不是法外之地”,不當行為若情節嚴重,甚至會受到刑法規制;另一方面,典型案例具有引領、示范、指導作用,相關部門可通過發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加強對網絡不法行為的震懾。
2、目前是征求意見階段,距離最終落地還需要大概多久?
上海瀛泰(臨港新片區)律師事務所主任翁冠星:
6月25日意見反饋截止,根據過去經驗的話,年內有望推出。
浙江曉德律師事務所主任陳文明:
征求意見的反饋截止日期通常為一個月。在征求意見結束,到法規公布實施之間,還有對送審稿的審查,有的要審查三次,有的審查一次即可,具體時問要看相關部門的工作效率如何。
正常情況下,三個月之內應當公布了。可以看到國家是非常重視本次征求意見,相信落地效率也一定是很高的。
圖源:最高法官網
3. 該怎么辨別網暴行為?什么程度該被“入刑”?施暴者會面臨多嚴重的懲罰?
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盧鼎亮:
網絡暴力行為與傳統的肢體暴力以及軟暴力有顯著區別。
網絡暴力在鑒別、界定、證據固定、網絡偵查難度、因果關系鑒定等各方面都有顯著特點。一般情況下,網絡暴力行為至少包括通過網絡方式肆意發布謾罵侮辱、造謠誹謗、侵犯隱私、貶損他人人格,損害他人名譽等行為。
對于嚴重的網絡暴力行為是會入刑的,符合特定條件的,可以誹謗罪、侮辱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故意毀壞財物罪、尋釁滋事罪、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等罪名定罪處罰。
比如在信息網絡上制造、散布謠言,貶損他人人格、損害他人名譽,情節嚴重,符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規定的,可以誹謗罪定罪處罰。網絡侮辱行為,如在信息網絡上采取肆意謾罵、惡毒攻擊、披露隱私等方式,公然侮辱他人,情節嚴重,符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規定的,可以侮辱罪定罪處罰。
對于組織“人肉搜索”,在信息網絡上違法收集并向不特定多數人發布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符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規定的,可以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定罪處罰。
將網絡暴力延伸至線下,對被網暴者及其親友實施攔截辱罵、滋事恐嚇、毀壞財物等滋擾行為,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條、第二百九十三條規定的,以故意毀壞財物罪、尋釁滋事罪定罪處罰。
4. 從落地角度來說,會不會出現“法不責眾”的情況?
北京卓緯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孫志峰:
一般不會。
以誹謗罪為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將明知是捏造的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在信息網絡上散布,情節惡劣的,以“捏造事實誹謗他人”論;也將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以及被轉發次數作為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據。并沒有將惡意轉發、傳播他人捏造的事實的網民排除在犯罪主體之外。
民事侵權的認定更是如此。因此只要構成犯罪的,就應被依法追究法律責任,這也是一個法治國家應有之義。
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盧鼎亮:
目前,有些網絡暴力的參與者正是抱著“法不責眾”的心態參與到網絡暴力中,再加上網絡暴力在確認加害人、證據收集、證據固定、自訴程序與公訴程序銜接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難度。
因此,出現了一些網絡暴力的組織者、參與者存有“法不責眾”以及“反正也抓不到”的僥幸心理。
但是,隨著偵查技術的快速發展、對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決心的加大、對網絡暴力惡意發起者、組織者、推波助瀾者以及屢教不改者進行重點打擊意識的增強,網絡暴力民事維權、公安機關協助取證制度的推進、網絡暴力立案監督力度增強,人格權侵害禁令制度的推廣落地。
通過對網絡暴力的嚴肅執法,是能夠切實矯正“法不責眾”的僥幸心理。
浙江曉德律師事務所主任陳文明:
《征求意見稿》主要分為以下四個部分:
1.充分地認識網絡暴力的危害;
2.準確地適用懲戒網絡暴力的法律;
3.提高懲戒網絡暴力犯罪訴訟程序的效率;
4.落實各個懲戒網絡犯罪的工作要求,并且要完善綜合治理網絡暴力的措施。
近期網絡暴力慘案頻出,我認為本次出臺的意見展現了國家對于治理網絡暴力的決心和信心,可見“法不責眾”這種情況大概率是不會出現的。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這句話將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位中國公民的心中。
5. 目前針對網暴的懲罰,在法律上是如何規定的?受害人在維護自己權益時,在實際操作過程面臨哪些困難?
上海瀛泰(臨港新片區)律師事務所主任翁冠星:
從專業角度來看,意見的出臺為阻止、懲治網暴行為提供了法律依據和執行依據。
目前針對網暴行為,并沒有法律規定,而是當事人只能通過散落在不同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中的規定進行維權和索賠。
這要求當事人具備非常專業的法律知識儲備,并且對當事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舉證責任要求,事實上使得應對網暴違法行為的維權成本非常高。
意見出臺后,我認為,當事人對于網暴行為無論是追究民事責任,還是有關部門追究施暴者的刑事責任乃至行政責任,法理上更為通順,舉證責任更為清晰。索賠、追責和懲戒措施的完善和執行的通暢,會更有效地震懾施暴人。
北京卓緯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孫志峰:
受害人維護自身權益時,主要存在侵權主體確認難、取證難、固定證據難、司法裁判尺度不一等困難。
比如,雖然國家通過各類規范性文件要求網絡實名制,但平臺在受害人提出投訴控告時,往往以與用戶簽訂保密協議等理由,拒絕提供侵權主體的身份信息,導致受害人無法直接針對侵權主體發起維權。
再比如,刑事自訴案件立案條件苛刻,受害人往往不具備在網絡環境下取證和固定證據的能力,更無法將符合自訴條件的證據備齊,刑事自訴案件成功幾率渺茫。
《2021年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研究報告》顯示,未成年網民在網上遭到諷刺或謾罵的比例為16.6%。按照《征求意見稿》,針對未成年人實施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應當從重處罰。(圖源:報告截圖)
6. 前述意見主要聚焦網暴的施暴者和受害人,如何理解網暴過程中平臺的責任?如社交媒體、短視頻平臺等,法律層面將有何種監管?
上海瀛泰(臨港新片區)律師事務所主任翁冠星:
網絡平臺的責任將進一步增強。
網絡平臺有義務對于用戶發布的信息和內容進行篩選,對于屬于網暴的信息,平臺需要第一時間采取隔離、刪除、屏蔽、淡化、禁言、封號等手段,將網暴所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果盡可能壓縮到最低。同時對于網暴信息,要及時配合公檢法進行存檔、取證等。
此外,互聯網平臺主張“避風港”原則也將受到一定限制,不能因為這些信息是用戶上傳,平臺已經刪除,再主張免責。平臺有義務防止負面效果的擴大。
關鍵詞:
- 這些“鍵盤俠”有治了:關于網絡暴力的罪與罰,業內稱有望年內落地_當前熱點 本文來源:時代周報作者:王晨婷數次悲劇之后,網絡暴力行為或將迎來嚴
- 養老金短缺?這場論壇上,專家建議養老金融多從家庭想想辦法 隨著人口壽命延長,全球老齡人口的比例將繼續增加,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
- 每日速遞:2023高考今日落幕,多地公布志愿填報時間 10日,2023全國高考將全部落幕,目前,全國多地陸續公布志愿填報時間。
- 31省份5月CPI出爐:11地漲幅低于全國,9地物價降了! 日前,國家統計局公布了31省份2023年5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中新經
- 認準這些高校!2023年山東具有普通高等學歷教育招生資格高校名單 山東省教育廳關于2023年山東省具有普通高等學歷教育招生資格高等學校名
- 當前頭條:杰克辣條敢在在國外虐待動物嗎?來,排排隊:美國7年,新加坡韓國3年,... 杰克辣條(真名:徐某輝)虐貓事件,在國內輿論場一石激起千層浪。
- 全球新消息丨20個驚艷世人的文句 0101種下一盆花收獲一屋的童話種下一段成長收獲一路的風光02春爭日
- 每日時訊!【原】中華詩詞大講堂‖第八十八卷:七絕·春日閑吟三部曲系列作品雅輯 中華詩詞大講堂第八十八卷七絕·春日閑吟三部曲系列作品雅輯之六(5
- 【原】初中第一個家長開放日 感受和小學大不同 上周,參加了娃上初中后第一個“家長開放日”,那感覺,和小學太不
- 了解牙髓活力——探索臨床試驗和組織學分析 世界熱資訊 評估牙髓的活力對于確定牙科疾病的適當治療方法至關重要。傳統上,臨床
- 環球今亮點!肺腑之言之肺占位影像診斷及鑒別診斷 ???????????????????????????????
- 江蘇金湖:水中生“金”,水蛭養殖探出產業發展新路子|熱推薦 近日,在江蘇省金湖縣復興圩農場有限公司水蛭高效養殖園區里,職工
- 世界看熱訊:《外科證治全生集》的陽和湯 圖 文 閑云感恩生活陽和湯,出自清代醫家王德維所著的《外科證治全
- 集成吊頂品牌前十名價格表_集成吊頂品牌前十名 1、集吊頂前十名品格2、奧華3、友邦4、奧普5、獅龍6、容聲7、格勒8、美
- 天天速遞!中國留學生服務中心學歷認證_中國留學生服務中心 1、中國留學服務中心,是教育部直屬事業單位,以事業單位法人注冊。2、
- 天天即時:比藥明康德還牛,博騰股份,業績持續爆發,2023年Q1再度超預期 在之前的文章中《價值事務所》有講,2023Q1是疫情放開后第一個完整的季
- 每日快報!四部門出手!消費再迎新政策 聚焦這兩大主線 6月9日,商務部、國家發改委、工信部、市場監管總局聯合發布了“關于做
- 邊緣計算領域步入高速發展階段 5月份以來超百家機構扎堆調研7家公司 今年以來,邊緣計算板塊持續走強,年內累計漲幅達43 25%,跑贏上證指數
- 6月9日基金凈值:華富強化回報債券(LOF)最新凈值1.685,漲0.24% 該基金的基金經理為尹培俊,尹培俊于2014年3月6日起任職本基金基金經理
- 北京市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召開貸款中介自律規范閉門座談會 從業機構要充分認識到行業自律規范的必要性,不能對現有問題視而不見,
資訊
-
 看點:創維數字(000810.SZ):pancake系列VR產品采用市場上已量產的最高端XR芯片高通XR2
格隆匯6月8日丨有投資者在投資者互...
看點:創維數字(000810.SZ):pancake系列VR產品采用市場上已量產的最高端XR芯片高通XR2
格隆匯6月8日丨有投資者在投資者互...
-
 滿坤科技(301132.SZ):公司PCB產品已廣泛應用于數據中心相關存儲和傳輸設備、電子...
滿坤科技(301132 SZ):公司PCB產...
滿坤科技(301132.SZ):公司PCB產品已廣泛應用于數據中心相關存儲和傳輸設備、電子...
滿坤科技(301132 SZ):公司PCB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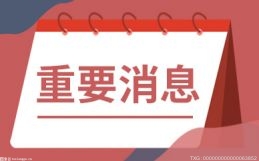 1-4月我國互聯網業務收入是多少?同比有增長嗎?
工信微報:2023年1—4月互聯網和相...
1-4月我國互聯網業務收入是多少?同比有增長嗎?
工信微報:2023年1—4月互聯網和相...
-
 十銓科技首次使用120mm一體式水冷了嗎?你知道具體參數嗎?
十銓首次使用120mm一體式水冷,純...
十銓科技首次使用120mm一體式水冷了嗎?你知道具體參數嗎?
十銓首次使用120mm一體式水冷,純...
文章排行
圖賞
-
 【原】初中第一個家長開放日 感受和小學大不同
上周,參加了娃上初中后第一個“家...
【原】初中第一個家長開放日 感受和小學大不同
上周,參加了娃上初中后第一個“家...
-
 集成吊頂品牌前十名價格表_集成吊頂品牌前十名
1、集吊頂前十名品格2、奧華3、友...
集成吊頂品牌前十名價格表_集成吊頂品牌前十名
1、集吊頂前十名品格2、奧華3、友...
-
 全球即時看!山東航空退市成定局!上市23年市值跌去九成,國航伸援手
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上市23年,...
全球即時看!山東航空退市成定局!上市23年市值跌去九成,國航伸援手
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上市23年,...
-
 全球播報:農村違法建筑的法律依據
當事人在無土地規劃、準建手續的情...
全球播報:農村違法建筑的法律依據
當事人在無土地規劃、準建手續的情...